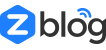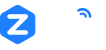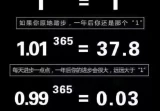文/张岩
一
如果不是把你伪装起来,我知道普天下的人都会看到我的残疾。我不愿让别人看到,不愿让一个“废”字轻易地把我的心刺穿。亲爱的,请原谅我伪装了你。因为你的与众不同,我没有勇气把你展示出来。我知道我伪装你,其实是在伪装我自己。
打从娘胎里出来,你就跟着我,不离不弃,默默无声,跟了我四十多年,直到现在。我对你的最初记忆是这样的:那时,我大约六岁吧,我和哥哥在太阳底下玩黄豆,我的穿着蓝碎花褂子的年轻而美丽的母亲坐在我们身边纳鞋底。母亲不经意间看出了我和哥哥不一样的地方——左手。哥哥两只手玩黄豆,而我只用右手玩,左手低垂在一边不动。于是我在母亲的怀抱里开始了求医的历程,也开始了我的眼泪多于欢笑的童年。我记得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次哭是因为举手。那天,哥哥举右手说:“毛主席万岁!”我学着哥哥的样子,也举右手说“毛主席万岁”.哥哥又举左手说“毛主席万岁”,我再举左手时,却举不起来了。我用了好大的劲,我的左臂却纹丝不动。我急得哭了。我抓了哥哥的脸,而后我又抓了母亲的脸。那年我七岁。从此我明白了一件事,我的左手跟别的孩子的左手不一样。
我哭的时候,你是否也为我难受?你无声无息地垂挂在我的左边,以不争的事实,成了我有别于其他孩子的残疾的左臂,也成了我淡泊人生中不能更改的胎记甚或是烙印。
你知道吗?我哭的时候,母亲也在哭,她是偷偷哭的,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哭。后来母亲就不哭了,总是把我揽在怀里,在灯下抚摩你,看你。为我洗澡的时候,先为你洗澡;为我剪指甲的时候,先把你的指甲剪了。再后来,母亲驮着我,从村里到镇里到县里,再到市里到省里,为你治病,母亲这一驮就驮了三年,可是终未治好你的病。母亲问医生,真的没有希望了吗?医生说,没有。母亲一下子泪流满面。
医生说,你患了小儿麻痹后遗症。你的肌肉萎缩了,你比右臂瘦小很多,不好看。我把你隐藏起来,隐藏在袖管里,除了我和母亲,我不会轻易地让别人看到你。就是从那时起,我学会了伪装。伪装你,伪装我自己。
二
你一直跟着我,跟着我走进了学堂。你知道吗?走进学堂的一刹那,面对几十双星星样的眼睛,我的脸多红啊。我怕他们看到你,从而取笑我。因为你,我怕上体育课。同学们到操场上去了,我却躲在教室里,把窗户和门都关上。后来有一次,我还是被校长发现了。我没有勇气出卖你,我只说我感冒了。第二天,全校师生大会上,校长点名批评了我,并把我叫到台上亮相。众目睽睽之下,我像被扒光了衣服,羞得无地自容。后来是怎样散会的,我记不清了,我只记得我带着你,躲在厕所里哭了一场。那时我念初二,已有了自尊。
因为你的丑,我受了伤害。很长时间里,我怨你、恨你,我总想把你藏得更隐蔽一些。我讨厌你,我不想再见到你,我害怕见到你。可是那次在家里洗澡,在衣服脱光了之后,我还是要不可回避地与你面对。看着你,我震惊而沮丧。你那么软弱无力地存在着,在我眼里是多么陌生啊。你是谁的?为什么跟着我?那一刻,我甚至有了自残的念头,我想,如果有一把刀,我会拿起刀把你砍下来,扔得远远的。我恨你,你却不动声色,还是那么死心塌地地跟着我,我看你看到后来,心里就湿了。人不能没有左膀右臂,你再丑,也是我的左膀啊。
上初三时,因为你,我又有了麻烦,其实还不仅是麻烦,你甚至把我的前程和命运都改写了。
毕业前夕,我爱上了一个叫玫的女孩。因为你,我自卑,我爱她却不敢向她表白。当我最终鼓足勇气把一封简短的情书放进她课本的最后一页时,我发现她和另一个男生在月光下的小树林里约会了。
后来就是中考,紧接着就是毕业。她中考考得不错,远走高飞了;我因为你的存在,中专体检没有过关,只能回家了。
我待在家里,无所事事,整天躺在床上睡大觉。母亲端着饭碗进来,劝我起来吃饭,我假装睡觉,不理母亲。母亲唤着我的小名,唤着、劝着,劝到后来,我竟来了脾气,我说:“不要你管!”母亲端着碗愣在那里,愣成了一尊雕像。
傍晚时分,我去了荷花塘。荷花塘在村南,不远。我坐在塘边,看荷花,看荷叶,看荷叶下面的小鱼摇头摆尾游来游去。我慢慢地转过头,竟看到不远处母亲站在榆树后面,向我这边看,袖口在脸上擦来抹去。
你改变了我人生的路径,你让我不得不离开土地,不得不离开母亲,去了没有母亲的城市。
我还要伪装你,伪装我自己。
三
我把你伪装得很好,却还是因为你,我一次又一次地出丑。那次,在火车上,坐在我身旁的几个女孩玩手机,玩到后来,一个女孩尖叫起来,说她的手机丢了。于是几个女孩一齐把目光向我投来,我成了她们眼中的贼。我脸红心跳,如坐针毡。那丢手机的女孩说,你看到我手机没有?我说,没有。女孩说,对不起,请你配合一下,把你的左手伸出来。我说,不行!几个女孩几乎是同声说,伸出来!我还是没有勇气把无辜的你展示给她们看,那一双双眼睛都像刀子。我面红耳赤,和她们争吵起来。后来乘警来了,在他的要求下,我不得不把你从口袋里抽出来,送到那么多健全人的面前。羞愧让我闭紧了眼睛。再后来,乘警为我解了围,他要那女孩拨打丢失手机的号码,那女孩拨了,所谓丢失的手机在挂于窗前的一个小包里响起来……我去了洗手间,在那里,我重新将你伪装起来,然后,我抽了一支烟。
因为你的负累,我脆弱的心不仅自卑,而且敏感。那是一次编辑老师和文友的聚会,说笑间,我们谈到领导和座位的关系,一个文友就和我开玩笑,说我是领导,应该坐上座。“领导”一词,在常人听来,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名词,没有任何指向性,而对于我,听了就觉得格外刺耳。我的过于敏感的思索告诉我,这位文友羞辱了我。因为我不是领导,而只有“一把手”才是领导,他是笑我肢残啊。我很伤心。聚会结束后,我给编辑老师打了电话,向他诉说了这件事,说到后来,我委屈地哭了。编辑老师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,他像哥哥,和我们这帮文友相处得很好。他在电话里向我保证,那个文友所说的“领导”绝没有取笑我的意思,那个文友爱开玩笑,性格很好,完全可以把他当朋友相处……
因为你,我对于“手”字太敏感了;因为你,我离群索居;又因为你,我的老师把我引进一个健康而美好的文学圈子里。亲爱的,我是该谢你,还是该怨你?你之于我,是幸还是不幸?是上苍安排你来激励我并辅佐我人生的吗?
四
带着你,我回了一趟老家。老家老了,老家的母亲也老了。那个穿着蓝碎花褂子的年轻而美丽的母亲不见了,现在,母亲老成了外婆。我为母亲洗了头发,又为母亲洗了脚,为母亲剪了手指甲,又为母亲剪了脚指甲。母亲拿过剪子,把我的左手拉到她跟前,为我剪起了指甲。我看着母亲戴着老花镜为我剪指甲的样子,心里暖暖的,也酸酸的。泪光里,我又看到母亲驮着我四处求医的身影;看到母亲站在大榆树的后面偷偷地用袖子抹泪的情景。
夜里,躺在妻子的身边,妻子把我的左臂抱在怀里,哭了。我记得谈恋爱那会儿,第一次跟她见面时,她也哭了。那是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,她要看我的左手,我说不行,你要看我就把右手给你。因为她是个健全人,面对她,我有自卑感。她还坚持要看,我就伸出我的左手,给了她。她两手抚摩着我的左手,眼睛看着我的脸,后来就哭了。她说这么好的一个人,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对你?她在我怀里哭了好久,又说,你不要太难过,残疾又不是你的错。
再后来呢,纯朴、善良的她,做了我的妻子。她在老家照顾我的母亲,为我生儿育女,我在城里为我最爱的亲人苦苦打拼。
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家乡的澡堂里洗了澡。之前,我都是在家里烧水洗的。因为我怕,我怕你——我残疾的左臂被人瞧见。现在,我想我不怕了,因为母亲和妻子都给了我最大的鼓励。
在澡堂里,在众目睽睽之下,我脱光了衣服,终于,套在我身上四十多年的伪装被我扒得一干二净。我向澡池走去,许多人都在看我,其实,他们并没有笑我。
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。我把我的左臂洗了,把我的心洗了,把我的灵魂洗了。我想,明天,面对人生,我就可以轻装上阵了。
我要感谢你,我亲爱的残疾的左臂,你自始至终陪着我,让我体验到比常人多得多的人生滋味。当幸与不幸向我迎面走来时,我哭过,笑过;当幸与不幸在我背后走远,它们又成了我的财富。
谢谢你,亲爱的,我会永远爱你,胜过爱自己。